归化:各取所需、选择有限与尽己所能

成事坏事,不在于哪几个人。
撰文丨刘天谕
编辑丨张钦
郑洋(化名)挂掉了电话,继续他的工作。“没成。没成就白忙活呗。”他强调自己作为经纪人资历尚浅,但刚才的谈话已经不令他感到稀奇。
电话那头是球员乔尼(化名)的父亲。他和妻子都是中国人,移居国外后,他们迎接了儿子乔尼的到来。那时他们尚未取得所在国家的永久居留证明,因此乔尼出生时具有中国国籍。国内一般用“潜在归化对象”称呼乔尼这样的球员。去年夏天,郑洋找到他们,为乔尼联系了中甲某队的试训。
乔尼踢得很轻松,俱乐部喜欢这个刚满 20岁的孩子。比赛日临近,球队提前结束了试训,并托郑洋向乔尼介绍未来的待遇。“他听了也没说什么。”他们约定保持联系,等冬窗再回来试试别的球队。
双方再次想起这个约定是一年半之后了。郑洋要到今年 10月份才知道,试训后乔尼很快进入一所大学,读酒店管理专业。课程和训练的时间安排重合,他于是不再去训练场。
乔尼所在的国家 8月开始新赛季。在郑洋刚刚结束的通话中,他告诉乔尼的父亲自己发现乔尼没有进入球队的大名单,并表达了对乔尼身体状况的关心。那位父亲则向他转述了他们的家庭会议,“他说,爸爸,我想开个好车。”
“踢球满足不了孩子开个好车这么一个简单的愿望。”这个例子在郑洋看来已经足够说明一切:很多人走不到作为归化球员在赛场上被注视、被评价的那一步。

“对吧”是郑洋惯用的一种标点符号,他语速很快但吐字清晰,大学只考了英语四级,现在能用不止一种外语交流。“这不写名儿吧,”他反复确认,“不写名就可以说,聊天嘛。”
做归化业务是郑洋“另辟蹊径”的结果。他认为经纪人应该属于士农工商中的“商”,“排最后,地位比较低”,同时承担一种润滑剂的作用,让一切更流通。国内足球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他几岁到几岁哪个教练带的啊?这教练肯定跟你认识的哪个人认识。问一句就知道基本的水平了。”经纪人作为立身之本的信息差就派不上用场。而一旦有一个因为“时运不济”被埋没在低水平联赛的国内球员,“首先这样的人基本上就没有。然后你还得跟十个八个经纪人去抢,乱七八糟的,太卷了。”
在国外找一个踢二三级联赛,但够踢中超或中甲的球员对人在国外、能用外语交流的郑洋来说要容易很多。俱乐部愿意为他的信息和人脉付钱。他在金元时代末期入行,做成一单球员归化后发现“确实能挣着钱”,就把这一业务延续下来。金元留给他的印象是没人愿意把与球员签订的代理协议注册到足协,因为足协对代理费的百分比有规定,大家的约定普遍高于限额且乐于守约,“现在基本上都注册了”,但约束力仍然有限,“你没见过哪个俱乐部是因为欠经纪人钱通不过准入的吧?”
但他最近仍在忙归化。在他看来,成功率低、变数大,也不是很挣钱,却也把大部分人都拦出去了。那些“傻子、混子和骗子”,会选择忽悠简单一点的钱,会外语的则选择做国际转会,“这个赛道还是比较蓝海的,”他到这顿了一下,“那词儿是蓝海,对吧?”
王彦彬(化名)在一家中超俱乐部工作。“而且符合条件的高水平球员也不多。”他将类似意义的句子前后说了有四次。
没有俱乐部会设置专人负责球员归化,在王彦彬看来这也没有必要,因为仅仅涉及“十个手指头都能数出来”的几位球员。专门做归化业务的经纪人也很少,他们已经知道哪些俱乐部有钱且有热情,各个俱乐部的管理层也和几位常做归化的经纪人很熟了。尤其是每个中超俱乐部都有一个将非血缘归化球员注册为内援的名额,还没有使用这一名额的俱乐部会和经纪人走得更近。俱乐部之间、俱乐部和经纪人之间,维持着坦诚与防备的微妙平衡,王彦彬对此不愿多说,“彼此都有点保密的性质。毕竟是钱的事。”
六位外援同时上场对一个俱乐部的吸引力在王彦彬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任何中超俱乐部都对归化球员敞开着大门:能在场上多一个水平堪比外援且不占外援名额的球员,无疑是提升球队实力的捷径。
但是归化球员会得到外援标准的工资,从外援归化的球员,他的工资往往高于之前。外援工资是“中超俱乐部每年花销的大头。”王彦彬以此总结俱乐部对一个没有溢价的归化球员的渴望,“真正的问题是没钱。”
工资帽的存在让俱乐部接受球员的溢价成为可能。根据中国足协的规定,一名中超外援的顶薪是 300万欧/年,目前人民币与欧元的汇率是 1:7.7,即中超外援的最高工资为 2310万/年。俱乐部可以自行为入籍球员申报归属球员类型,国内球员平均合同薪酬不超过 300万/年,外籍球员合同薪酬总额不超过 1000万欧/年,即不超过 7700万/年。
正因如此,王彦彬表示,“即使你报价涨了,这些俱乐部也会很热心地琢磨一下。”他透露,某位归化呼声很高的球员就是卡在了俱乐部没钱,当地政府也不愿出钱上。但他的经纪人早已和其他俱乐部接触,多家俱乐部“说你来我这我立刻给你归化”,足协也在其中牵线搭桥。
溢价的合理性也得到了俱乐部的充分理解。一旦该球员在 21岁之后代表中国国家队参加了世界杯,根据国际足联的规定,他将失去代表其他协会参赛的资格。而入籍中国的球员,如果想通过转会的方式前往外国俱乐部踢国内联赛,可能要参与外援名额竞争或等待工作签证,生活上也会面临种种麻烦。
王彦彬仅仅倾向于一些“不要太贪”的球员。对于签字费和安家费,郑洋的第一反应是“谁出呢?”同时承认如果要求一个人做出改变,那这个人肯定会提一些条件。他们的观点统一在“没钱”上,王彦彬总结道,额外的待遇已经很难出现。
进入职业俱乐部是宋思明已经实现了的梦想。他为一家中超俱乐部工作到 2021年,现在是一位经纪人。老板和品牌部不喜欢负面舆论,宋思明说,所以那个俱乐部的每一个人都显得热衷于保密。出于一种责任感,他点了一杯冰美式在咖啡店里尽可能多地回答问题,“我相信你接触到的这个行业的人,能跟你把事情说清楚的也不多。所以这天然就有个壁垒,你还不给他挖几个管道,这个壁垒不是越来越深吗?”
他不喜欢“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花钱能买来他们的人买不来忠心”之类的说法,也不喜欢“只要中国队能赢,我管他谁来踢”的态度。职业运动与专业运动有着本质的区别,他说,职业运动员是一份工作,“如果我们带着这么强烈的荣辱感、代入感去渴望赢,去看职业运动员的时候就容易有心理落差。”
没人说清经纪人接触球员、接触球员的外方经纪人(如果有的话)以及接触俱乐部的先后顺序,因为更有可能的情况是所有事项在交叉进行。经纪人将俱乐部的合同拿到球员或外方经纪人面前,球员或外方经纪人接触不同的国内经纪人,用一个合同争取另一个更好的合同,国内经纪人拿着球员本人或外方经纪人的报价,向国内俱乐部四处放风,表示又有某俱乐部加入竞争,导致球员待遇需求更高,用哄抢的局面期待再次提价,然后用更优厚的合同吸引球员的注意。
这在宋思明看来非常自然,他顺着刚才的思路说,“职业运动就是一个市场化的东西,它发展到哪是哪。”

埃里克(化名)早早显示出了踢球的天赋。6岁那年,作为一个出生在中国的中欧混血儿,埃里克因为高大的身材在新加入的俱乐部中担任后卫。一位教练在他 7岁时将他换到前锋的位置上,“整个就有点英雄的感觉了。”埃里克的妈妈凯瑟琳(化名)评价道,“英雄”这个词在她后来的表述中出现了很多次。帮助一个从未得过冠军的球队在一场三人制比赛中进了7个球之后,10岁的埃里克和他的家人决定走上职业道路。
为了兼顾足球和读书,埃里克回到他父亲出生的那个东欧国家,从首都最好的俱乐部一路踢到国青队。初到异国的生活并不容易,凯瑟琳说,“他是一个突然飞来的小朋友,踢得又好,他们看他长得和自己也不一样。”教练和家长听不到孩子们在训练场上紧挨在一起时的对话,凯瑟琳不想给 15岁孩子的恶意打上某个国家的标签,只说埃里克有一天大哭着回来,告诉自己他又被骂了,刚才打了一架。
凯瑟琳从埃里克很小的时候就向他强调身份认同的重要,他会反复和她说,“我就是中国人。”从儿子的经历中她理解了这种选择,并告诉他“选择到根不容易,你要一直坚持。”
今年,埃里克已经 18岁。太多经纪人来过了,最近的一位甚至拜托国青队主教练促成一次见面。“可能有一条道路已经铺平了,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我们以为自己有选择。但是到了时间,有可能就是没有选择,那条路就是这样子,你按照那条路去走就可以了。”凯瑟琳说,埃里克暂时没有走到那个路口。
2014年,16岁的约翰·侯·塞特是挪超豪门罗森博格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联赛出场球员,挪威足协称他为“天才少年”,媒体将他与厄德高、阿热并称为“挪威三杰”。顺利的话,他会像今天的厄德高和阿热那样,加入挪威国家队,并在一家英超球队担任队长或主力。
后来,约翰·侯·塞特成了“中国第一位归化球员”,并得到一个中文名字:侯永永。此时距离那个帅气的天才少年闪亮登场已经过去五年。因为患有先天性髌骨高位,他的膝盖频频受伤,2017年他被查出急性心包炎,入院检查时他向家人说,“如果医生说我继续踢球只能活到 50岁,而不踢球可以活到 100岁,我会选择继续踢球。”
但他只能断断续续地把球踢下去,到了 2018年,人们只能在挪乙的一支球队中看到他出场。北京国安在 2019年 1月 31日与他签下了为期两年的合约,2020年他出场 8次,进球 2个,这是不错的数据,一切似乎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2021赛季,他因伤缺席了全部比赛,2022赛季,他仅仅作为替补,出场了几分钟。
挪甲球队兰黑姆在 2023年迎来了它的老朋友约翰·侯·塞特。今年,约翰·侯·塞特已经出场 25次,贡献了 16个进球、7次助攻,是挪甲 9月的最佳球员。他似乎再次找回了状态,或者说,这一次伤病没有过快地降临。
邓加洛(化名)发现侯永永的妈妈侯豫榕是自己老乡时曾非常兴奋。2015年 5月 21日,配上很多感叹号,他向粉丝分享了这一发现。在微博上更新埃里克们的近况是他从 2012年开始的一项爱好,目前归化成功的所有华裔球员几乎都由“Jallo-Tang”最先发现,为媒体录制播客时,主持人会在他的名字前加上“华裔球员研究专家”来介绍他。在只考虑水平,不考虑球员意愿的前提下,邓加洛对目前可归化的华裔球员总数做了悲观的预计。“不到 30人,”邓加洛说,“我最近在关注美国、西班牙这些国家的球员。家长们很热情,但水平可能和我们的预期有差距。”
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占全球华侨华人总数的 70%以上。除此之外,美国的华侨华人超过 550 万,欧洲估计有 250-300 万。这样的数字构成是邓加洛感到悲观的前提,东南亚国家的足球水平对中国难有助力,而所有在欧洲、阿根廷、巴西等地区的华裔加起来,数量可能都没有在美国人数多。
基数已经很小,邓加洛接触的大部分华裔球员在踢到一定年龄后又往往回到读书、找工作的路上。一个例子因为罕见令他印象深刻:已经被藤校录取的学生坚持走职业足球道路,得到家人的大力支持,“类似于,说我儿子能踢中乙他可以不上清华”。
同时职业道路也不因愿望强烈而铺开。在邓加洛看来,西班牙U19的某个强队,可能只有 2-3人能成为职业球员,踢上西乙,剩下的人将在退役与踢 3-5级联赛之间做选择。而一个队里能出现一个华裔球员、他又能走上西班牙的职业联赛,“这个概率可能就万分之一。”因为在关注华裔球员的十几年里,这样的球员他从没见过。
归化有血缘和非血缘之分主要是因为《国籍法》对入籍条件的划分。根据《国籍法》第七条,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或无国籍人,除遵守中国的宪法和法律外,还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中的一个:(1)中国人的近亲属;(2)定居在中国;(3)有其他正当理由。因为在没有血缘的条件下加入中国国籍相当困难,目前行业内对非血缘归化对象的选择往往是根据国际足联章程(FIFA Statutes)的“章程适用规则”(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Statutes)中“代表队参赛资格条款”(Eligibility to Play For Representative teams)倒推。郑洋说,“这个时候得足协同意了,(国家队)主教练也同意了,才有下一步。”
国际足联规定,非血缘归化球员在相关协会所在地区须居住至少 5年,才能获得代表该协会参加国际比赛的资格。因此选择非血缘归化球员时,在中国即将待满 5年的外援会得到额外的关注。
在 2018年之前从没听过“归化”这个词的李柱国(化名),对国家队启用入籍国脚这件事接受良好,具体到球员,他怀念 2013年“小圆脸爆炸头,一瞅就像小球星”的艾克森,但认为“我们归化的这些队员,第一个失败的就是艾克森。”因为从 2019年疫情开始之后他就“身体发胖、脸上发胖”,年龄大了、早已不在最佳状态。
类似的质疑宋思明已经相当熟悉,以至于话刚刚起头,他已经自动把问题补全解释下去。他用今年中超外援的平均年龄是 29.1岁说明当年选择的狭窄。《在场外》做了进一步的计算,考虑到一位球员从被关注到入籍的时间,所有在中国踢球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以此类推。由于港澳台足协与中国足协在国际足联属于平级协会,而外援的归化因操作复杂,往往以能代表中国国家队参加世界杯为标准,所以港澳台球员在这里被当作外援计算年龄。
这样计算,30岁以下且在中国四年及以上的球员只有周定洋、罗慕诺、梁诺恒、塞尔吉尼奥,真正的“十个手指头都能数出来”。中超外援的平均年龄是 29.3岁,他们大部分是今年的新援,在中国待到 3年及以上的有 28位(平均年龄 30岁),4年及以上的 11位(平均年龄 31.6岁),5年及以上的 8位(平均年龄 31.8岁)。
什么时候开始办球员的入籍手续是郑洋和王彦彬提到的同一个细节。如果球员还在国外踢球,手续突然办好了,他在国外生活会变得麻烦。如果等球员来了国内,赛季开始前入籍手续却没办好,因为中国足协不允许球员在一个赛季内变更身份,那么该球员一整个赛季只能作为外援使用。在很多情况下,王彦彬指出,“我们归化的华裔球员是达不到外援水平的”,所以那个俱乐部相当于一整年少一个外援。
他们都是在提到申花 2023年的外援晏新力时说到的这一问题,不过两人对晏新力的情况理解不同。郑洋强调晏新力不是自己经手,但他认为,出现这样的情况是球员、俱乐部和足协达成了一致,“你先来中超踢一踢,不是一上来就给你护照。中间我们通过比赛再评估。”最终的结果则是球员没有通过筛选。“要是阿贾克斯的主力来了,那肯定把他筛不出去。”
而球员一旦“来了”,融入会变得非常自然。翻译会跟在语言不通的球员身边,宋思明列出一连串生活琐事说明翻译、经纪人,或其他俱乐部员工的分内工作。除了保障球员的训练和比赛,还有办签证、体检、租房子、去银行开户、办电话卡、联系他太太生小孩的医院,帮他孩子找学校等等。长期自己在外生活的球员,一两周就可以“搞定”,已经成家的球员,俱乐部会再帮他们的家人重复一遍流程。基本上三个月到半年,外国球员就会有自己的生活圈,也会慢慢交新朋友。王彦彬说,“但凡有五年这坎儿,基本上中国文化啊性格啊,都认同得差不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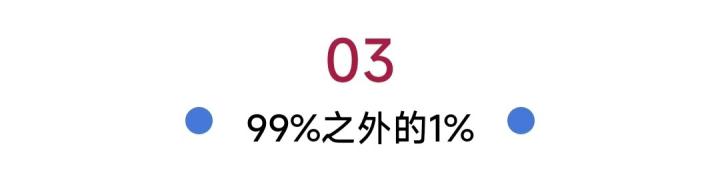
郑洋、王彦彬和宋思明不约而同地用“仓促”形容 2019年的归化,用“谨慎”形容今年的情况。宋思明评价 2019年说,“风口来了,你做不做。不做等于浪费了一个风口。” 2015年北京申办 2022冬奥会成功,不擅长冰雪项目的东道主后来选择了“归化运动员”这条在世界范围内反复得到验证的路,作为在七年后给观众一个交代的方式之一。
入籍涉及体育总局、大使馆、外交部、国家移民管理局、公安部等部门,除非得到行政力量的帮助,非血缘入籍因为条件严苛几乎被视为不可能。王彦彬多次提到,就算是血缘归化,经纪人和俱乐部在推动一位球员入籍之前也会和足协商量,得到足协背书,否则流程的长度首先就“没谱”,任何环节也都可能卡住——足协和各俱乐部在 2019、2020年做成的归化,是因冬奥会而生的归化大潮的余波。只不过在足球这里,被寄予厚望的是 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
2022年 5月 21日《足球之夜》发布了一期名为“入籍政策:艰难的选择”的节目,对 5名入籍国脚(艾克森、阿兰、洛国富、蒋光太、李可)和 4名本土国脚(武磊、吴曦、张琳芃、张玉宁)在世预赛中的出场时间和累计进球数做了统计,前者出场 2718分钟,进球 8个,后者出场 4727分钟,进球 19个。
对此郑洋评价道,“归化只能是在你整体有一定水平的基础上给你锦上添花。雪中送炭……我觉得连短期的解决方案都不是。”宋思明则将国家队比作树的顶端,他问,“树顶歪了是树顶的问题吗?”
洛国富说自己为入籍只考虑了十分钟。当时在中甲踢球的他,意识到如果想要加入中国国家队,至少要先在恒大踢上球。他开始将上午的时间也投入健身房,并因为压力养成了咬手指的习惯。2022年,他在镜头前展示自己的左手,“我的指甲几乎没有了”。艾克森揉着一只眼睛,说感到没有发挥自己全部的能力。“我不想找借口,但是经过很长时间的封闭,很多队友、包括我,都已经到一个极限了。”
宋思明和他说到了同一件事。他无意反驳以“进入世界杯”为衡量标准时 2019年归化的失败,但希望对当时的情况进行补充说明:首先是疫情三年的赛会制让中超的水平大幅度下降,其次,世预赛时球员们关在阿联酋三四个月,有几位国脚的健康状况出现了问题。
“没人同情你的,我们的文化是不同情弱者的。”他说完经手归化的俱乐部和获得上场资格的球员统统竭尽全力之后,又觉得自己的话没意义。国家队的水平在他看来本来就只有 60分,“发挥得好 65分,发挥得不好 55分,世界杯是 70分才能考上的东西。突然楼上装修,连装三个月,就只能考 45分。”
中国队“考了 45分”输给越南之后,3亿球迷的愿望破灭了。那个后来在央视反腐纪录片的镜头里哭诉无后悔药可买的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也感到破灭。他曾期待国足进入世界杯,那将是令人羡慕的政绩。在 2018年的赛季总结大会上提出“未来中国足协将积极推进优秀外籍球员的归化工作”的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也和陈戌源出现在了同一个纪录片里,比他早几分钟亮相。
可是宋思明仍然很难说出到底是“谁”的问题。李金羽也觉得难以说清,2023年 8月懂球帝的记者采访了他,被问到如何看待这次的足坛风波,他说,“你要说这几个人能改变中国足球……我觉得还是路漫漫吧。”
“一方面是觉得花了那么大代价,结果没什么效果。一方面是知道领导收了不该收的钱,想要避嫌。”王彦彬这样推测足协现在的态度。因为不见对于归化的明确表态,强调自己和足协关系疏远且不涉足归化业务的宋思明追问,“万一现在上面那道门根本没开呢?”
在不考虑上级部门态度的前提下讨论归化问题,在宋思明和王彦彬看来完全是球迷、媒体、俱乐部“在自嗨”,没有意义。“那么高层级的东西,过去又惹了那么多非议,现在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急迫性。”宋思明说,如果纯粹从办事的角度看,他觉得“这根本不靠谱。”
据郑洋和王彦彬了解,归化目前不是禁忌。郑洋说,“他们(足协)也就是中层工作人员,权限有限,也是要向上汇报的。这些人,”指目前热门的几位归化球员,“实际上啥也没耽误。”
他还提到从今年开始足协在建立海外人才库,主要关注十六七岁的华裔球员,经纪人会定期与足协更新球员的年龄、位置、所在俱乐部,以及是否已经有中国身份、代表中国国家队踢球的意愿等信息。王彦彬表示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但每次他与足协的人谈起某位潜在归化对象,“他们能反应上来是谁。”
郑洋曾为与苟仲文的一次见面作准备,遗憾的是在成行之前苟局长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上CCTV了”。他最近因为在忙归化和足协新一批工作人员有很多接触,他们的表现令他满意,“也跟咱们一样,是普通打工人。而且真的是在权限范围之内很努力地工作了。如果真是大家刻板印象里的尸位素餐、成天混日子,很多事情他们其实不用做的。”他曾被足协邀请作为中间人与某位受到球迷关注的可归化球员接触,说足协“不止找了我一个人,是一大波人,把人家找烦了都。”
郑洋、王彦彬和宋思明都为归化提了一些建议,比如效仿一些西亚国家,如沙特,规定外援中必须有两位U21选手,扩大归化的选才面。“但我个人倾向于不要老去想这些事情。”宋思明说,“大的方向不是由我们这些细枝末节能影响的,我们只是那 99%之外的 1%。我们只能基于现有的条件,在各自的领域发挥自己最大的能力,希望这事能好。”
